徐则臣:四个住处一个家
本文选自徐则臣新浪博客随笔《生活在北京》
文:徐则臣
在北京六年多我住过五个地方,除了现在我端坐其中敲键盘的家,之前四个我更习惯依次称之为「宿舍」、「小屋」、「芙蓉里」和「海淀南路」。
宿舍在万柳学生公寓,北京的西北角。0二年我来报到,出租车司机绕了半天才找到一个尘土飞扬的大工地,马路修了半截子,很多年轻人拎着行李在一幢巨大的楼前出入。司机说,只能是这里。那时候海淀区政府和公安局还是一片荒地,中关村三小尚无踪影,康桥水郡、万城华府等高档社区的地基上散布着低矮破旧的平房,工人们走在尘土里。完全是都市里乡村。这样的北京我有点接受不了,太不像样了。当时我对「都市化」的想象还停留在小城镇阶段,以为这个地段要繁华起来,那是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。但只几年过去,不变的就只是公寓西边的昆玉河水在流,忽如一夜春风,高楼从大地上长出来,半空里是楼房,地上挤满了人和车,成了都市里的都市。那时候我不知道楼房是都市的先遣队,它们开到哪里,「都市化」便会立马将周围占领。
与宿舍隔一条马路的是万泉新新家园,还有一个我忘了名字的高档住宅区,据说住着柳传志等人。当时的房价每平米八千,我们同学都觉得贵得离谱,现在据说已经好几个八千了。老同学聚会说起来,拧胳膊拍大腿地后悔,要是当年咬咬牙跺跺脚买上一两套,哥们今天就是好几百万的富翁了。可是,哥们当年在哪呢,买双拖鞋都得挑最便宜的。
过了昆玉河是远大路,我站在西向的窗前看河对岸金源购物中心一寸寸建起来。传说是亚洲最大的超市,我就奇怪,如此庞大的超市有多少东西可卖呢。觉得建得挺花哨,周身用了很多种颜色的瓷砖。建成了,我和同学瘪着口袋去参观,哪里是什么超市,空间分门别类无数块,卖什么的都有,当然都是高档的,小吃的价钱也相当可观。建造之初附近的有钱人没现在多,生意颇有点冷清,小吃店的师傅和服务员趴在餐桌上打瞌睡。前两天我又去,厕所里人流都不断,才几年啊,日子就好过成这样。吃过晚饭我常去里面的纸老虎书店,翻完这本书再翻那本,肚子里消化得差不多了就打道回府。除了打折,坚决不买书。

另一个散步地点是昆玉河边,沿着水走身心通泰。尤其夏天,看水看船看人坐在河边的大排档里喝冰镇的啤酒。酒我没兴趣,羡慕的是黄昏降临时他们所有的安宁的时光。即便现在,一到夏天,置身琐碎喧嚣的生活里时,我都时时有去昆玉河边坐一坐的冲动。端一杯冰镇的扎啤,看世界以椅子为圆心慢慢地向四周静下来,你们疲于奔命地跑,我希望世界慢下来。慢下来。河边要建成北京的大氧吧,一直有此传闻。我不知道大氧吧到底是个什么样子,纳闷的是万柳之地柳树甚少,昆玉河边倒还有几棵像样的,马路两边的全是瘦骨嶙峋,比手指头粗不了多少。现在应该好一点,因为柳树长得快,起码三五年之后,那些营养不良的小柳条至少看起来像柳树了。
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宿舍,3区534室。去一趟北大很麻烦,公交332支线兼作校车,早去晚归的人很多,挤不上正常。后来校车多了点,课又少了,更不需要去学校了。现在想起来,我好像一年到头坐在那把廉价的电脑椅子里。食堂在楼下,打了饭上来吃,如果没有别的事,找不到理由离开那把椅子。闹「SARS」的时候封校,停课,我在宿舍里结结实实坐了近两个月。疯狂地下载电影看,隔壁的一个同学据说那段时间看了一百多部。那段与世隔绝的时光是我的好日子,看完电影我开始写长篇小说《午夜之门》的第一部《石码头》,断断续续又写了其他几个小说。能有大块时间来写作,我感到幸福。这一天是你自己的,这一天你可以只干一件事。当时的北京前所未有的清静,马路上人烟稀少,公交车空空荡荡地开,救护车的叫声让人心惊肉跳。我们每天量两次体温,傍晚在楼下领取一袋校医院煎制的中药,喝下去为了抵御病毒。晚上我们会三两个人结伴散步,在空荡荡的马路上空荡荡地走。
这是我在北京最安静的日子。马路上的空,和08年春节有点像。因为买了房子,欠一屁股债,加上回去的车票紧张,08年的春节我决定在北京过。这也是我头一次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过年,夜晚爆竹和焰火此起彼伏,我从网上断断续续地看春节晚会,感到了被遗弃的凄凉。大年初一走到中关村大街上,半天看不见一辆车,其冷清让我想起「SARS」。但那时候的冷清和恐慌要全北京人乃至全国人民来承担,所以我感到的是安静;而现在的冷清只有我一个人守着,我觉得凄凉。我一直不喜欢「京漂」这个说法,但那几天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「漂」着,晃晃荡荡,和一个可靠的背景失去了联系。

第二个住处「小屋」,在北大,未名湖畔的镜春园,那个大院子住过嘉庆皇帝的四公主,门前有两棵大槐树。大门从清朝以来就在腐朽,朱漆剥落,但仅从残木和斗拱的规格也不难想象当年的富贵繁华。院子里有柿子树,深秋主人用剪刀和长竹竿打柿子,底下有人拿布兜子接应,我在旁边看。红通通的柿子很诚恳,叶子落尽只有果实挂在枝头。我租的房子嘉庆皇帝的四公主从没见过,她不会想到仅靠砖头、楼板和石棉瓦就能搭建起一间五平米的小房子,而且租金每月要八百元人民币。这间房子建在院子里,单砖跑墙,屋顶倾斜,冬冷夏热。我住进去的时候是秋天,室外温度适宜,进了小屋就寒气逼人。房东住在高大的房子里,当年四公主裙裾在其中贴着地面舞动,可以设想房间里一定四季如春,所以房东迟迟不烧暖气。而我在小屋里从中秋就盼望暖气进来。整个秋天我都住在里面,直到冬天,那是我在北京待过的最冷的房间。
但是我喜欢未名湖,能枕湖而居,就算附庸风雅,冷一点也值;虽然没有践行当初的宏愿,每天环湖漫游。清冷的早上我去湖边读英语,看起来很像个勤奋的学生。晚上去图书馆或者自修室,十点左右沿湖边回小屋。有一个节日晚上,博雅塔装点上彩灯,湖面上漂荡很多纸船,我忘了那是什么日子,只记住了那晚未名湖幽艳鬼魅,有别一番意味。那段时间我学习认真,除了日记和功课,别的东西不写。我憋着,准备忙过这阵子再动手,写小说也写散文,散文的题目都想好了:《未名湖、小屋和整个秋天》。但终于没写出来。所以,湖边的小住留给我的,风雅、寒冷、外语和一些不高兴的事之外,就是一篇想象中的散文。我在那里住了不到三个月。
毕业后租的第一处房子在芙蓉里,六楼,两年,从楼梯的窗户可以看见楼下的万泉河公园。租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它靠近北大,我可以去北大的食堂吃饭。多年来我都无比热爱食堂,因为有消毒餐具,吃完饭连碗都不要洗。我可以就近去图书馆看书,去大讲堂看电影和演出,去听平常难得见到的大学者的讲座,可以去中文系继续参加师生们的讨论。这是两室一厅的房子,与一个做书的朋友合租,共用厨房和卫生间。我跟房东说,我们都没什么钱,价钱别整得太高。事实也如此,那时候很穷,逛书店尽量不带钱。现在我还怀念那地方,周围有很多书店,是我晚饭后散步的好去处。北大里面的书店,旁边海淀体育馆里的第三波书店,公园边上的采薇阁旧书店,还有海淀桥边上的巨大的中关村图书大厦,我住的第二年,第三极书局也开张了。一周里所有书店都可以轮上一遍。
这房子的另一个好处是,过了马路就是公园,适宜散步、乘凉和晒太阳,夏天晚上每周末还能看两场露天电影。穿着拖鞋夹松散的观众里,我恍惚回到多年前的乡村,而露天电影即便在乡村,也绝迹多年了。公园角落里装备了各种健身器材,每天晚上都要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健身运动,以老太太居多。她们健身的时候,旁边经常蹲着阿狗阿猫,宠物比子孙更忠实于这些老人。我一直很想荡西北角的那架秋千,但一跑到那里就发现上面坐着两个小孩。作为叔叔,我不能跟他们抢,我就接着跑两圈,然后出了公园去采薇阁。我在好几个小说里写到这个公园,重点是喷泉广场边的很多块大石头,乍一看很有点像英格兰巨石阵。喷泉我记不得是否看见开放过,倒是有很多运动爱好者在上面练习轮滑。公园里从来少不了情侣,他们当然躲在小山包的后面或者树丛里,至于躲进去干什么,我没好意思看。

住在这里我觉得身在民间。周围有很多老房子和老住户,有大批的外来房客和民工,我可以在去西苑早市买菜的路上看见各色人等,办假证的,卖盗版光盘的,假古董贩子,小商小贩,在北大旁听的外地青年,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的民工。到了晚上,他们会聚在承泽园门口的麻辣烫和烤串摊子前解决晚饭,满满当当的热闹的烟火气。我很喜欢那种过日子的感觉,喜欢看他们坐在小板凳上,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和烧饼,然后爽快地大喜大悲大声笑骂。我也常常凑上去吃两串麻辣烫和烤肉。我写过一些关于他们的小说,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,照理说他们与我的工作和生活不沾边。
为什么就不能沾边?离开北大,下了班,我还得过日子,身边生活的就是这么一帮普通人。这个世界上这些人毫无疑问是大多数,我不是中产阶级,也没法小资,高官和巨富都不靠,也不住高尚社区,出门碰见的只能是他们。你不能因为他们是办假证的、卖盗版碟的就对他们另眼相看,他们也是普通人,可能比你我都正常,不过是职业貌似有点古怪而已。要说为害社会,哪个贪官和奸商不比他们罪孽深重?我也从没把他们当成什么「底层人物」来写,在我看来他们就是一个个「人」,有我的亲朋也有我的好友,跟他们聊天我没有心理负担,也不必藏着掖着,他们比我还好说话。在北京,宾馆、酒吧、夜总会和高尚社区是一个人间,很多人围着个麻辣烫的摊子也是一个人间,热气腾腾的烟火人间。我写他们,因为我在其中;我写他们,因为他们在我身边。我不想替他们诉苦,也不要为他们哭穷,我只是想实实在在地把他们写出来而已。
在芙蓉里,读书时的那台杂牌台式电脑和廉价电脑椅继续跟随我战斗。这里是北京市海淀区,我的关于北京的小说中,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这里。我在小说里不断重复这个地名,海淀,芙蓉里,当然还有北大、西苑、苏州街和中关村大街,等。我一直住在海淀区,相对于朝阳区、宣武区、东城区和西城区,我对这地方更熟悉一些。0六年我写了一个中篇叫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,写的时候我住在芙蓉里,写完了,我搬到了中关村。

海淀南路2号楼6门,五楼的一个两居室。租金不低,但对于这一带的市价,已经很便宜了。北京最好的大学、中学和小学都在周围,租房的学生和家长排长了队,价钱就直往上跑。站在窗前我能看见人大附中的学生在校园里走动,看见他们在操场上打篮球。在所有的运动中,篮球是我最喜欢的项目,来北京之后,已经几年没摸过篮球了。我想这下好了,可以每天傍晚去附中打球。女房东北大中文系毕业,高我若干级的师姐,为了感谢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租下这套房子,我给师姐送了本小说集。
下楼出门左拐就是中关村大街,我对这条街充满了莫名其妙的好感。每次想起这个名字,我就觉得会有源源不断的故事可以讲。我要在靠近中关村大街的地方好好地讲几个好故事。两居,意味着可以拿出一个房间来作书房,如此美好,我把打好包的书解开,一排排摆进书橱。我喜欢看见成排的书上架,三天两头往书店跑大概就跟这个奇怪的爱好有关。现在回头数点,已经记不起来在海淀南路的一年里写了多少东西,不多,但也不会太少,有几个故事我还是比较满意的。我开始有了「生活」的感觉。一个家需要的所有东西这里都有,除了电视,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电视的习惯了。在我的感觉中,「家」和「生活」息息相关,但我还是不习惯称这租来的房子为「家」,我在「生活」,在「海淀南路」。下了班,朋友聚会结束,他们理直气壮地回「家」,我说,我回「海淀南路」。就像住在芙蓉里时,我说我回「芙蓉里」。区别于作为「宿舍」的万柳公寓和湖边小屋,「芙蓉里」和「海淀南路」的定义介于「宿舍」和「家」之间。其中艰难而又漫长的过渡,已经标示了我在北京生活的深入。
0七年年末和0八年上半年,我经常站在海淀南路的窗户边往东南看,越过人大附中的教学楼可以看到中关村大街边上的一幢居民楼,我新买的房子其中的某一层。小区的地址上要写「中关村大街XX号」,我在一点点靠近这条街。装修,采买家具,琐碎的细节如此烦人,不过我提醒自己耐心点,再耐心点,一个真正的「家」在慢慢长成。我按照我的设想去布局房子,把家具的尺寸精确到厘米,比较地板颜色最细微的差别,好了,一个第一眼看上去让我想哭的破旧的房子的壳,变成了温润丰满的家,我想要的一切这里都有,或者即将出现,我的手经过墙壁、家具和阳台上的双层玻璃,觉得身体里某个飘荡的东西慢慢落地。我不再需要在每年的七月份为下一个住处发愁,不需要再去网上、房屋租赁公司和朋友那里打听,哪里有适合做我临时的窝。

还在为租房发愁的朋友质问我,拿什么买的房子?我说,在北京这地方,穷人买房子要的不是钱,而是胆量,只要你敢借债。我东拼西凑,背高高的债,我想来日方长,有足够长的时间去一分分地还。我不想整天为一个窝伤脑筋,不想因为过段时间还要搬家,就让一大堆书和其他的物品委曲求全地待在上次搬家就打好的包里,此刻码放在墙角或者床底下——而为了找一本书,我常常要把所有地方都搜查一遍,拿到手时阅读的兴致已经没了。在我自己的家里,我要让每件东西都待在它该待的位置上。想到它时,头一歪,在那儿呢。所以我订做了六个书橱,让它们一直高到屋顶,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们全都解放,一一归位。
房子装修好,晾着跑味的那段时间,我和家人每天从海淀南路往新房子里运书,蚂蚁搬家似的,运一点摆放一点。看见书橱里日渐充实起来,我背着手在书房里转来转去,这是我的房子,我的家,看这一排排的书,我觉得自己像个有学问的老地主。老地主们一天三次来到自己田头,跟我一样想,看,这一顷顷的地,这茂盛的庄稼,全他妈是我的,今天我想吃米就吃米,明天想吃粗粮了,咱就改吃山芋和高粱。这日子很好。比进书店看那成山成海的自我叫卖的喧嚣货物感觉要好得多,在自己家里,我从书橱里抽出的每一本书都是我想看的。
然后我搬家,从「海淀南路」搬到了「家」里。三十岁这年,我有了稳定的卧室、书房、厨房、洗手间和生活,不用担心催缴房租的电话,不需要再看房东恩赐般的脸,我可以改装和修正家里的所有东西,包括我的生活。

编辑|ludanty主编|寿佳茵
总编|喻潇潇 顾问|王淑琪
推荐阅读
点击下列标题 阅读更多冯叔专栏
美女老板 |泼妇|牛的性生活|悼念则西
管理自己|潜规则|赌场|男人的人品|底线
受苦是福气|人生的进与退|孤独
子宫|底裤|庸俗和堕落|凤姐
坟墓和鲜花|女人永远是男人的老师
-商务联系-
阿牛|13311153963
微信|niuniu-fengmani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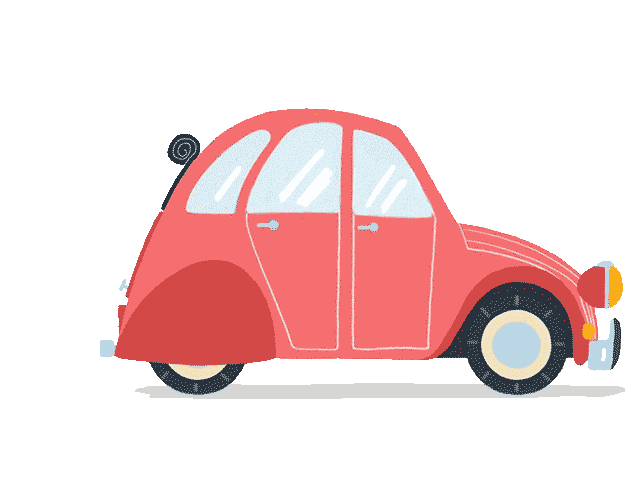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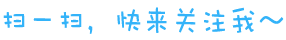

-

凤凰网汽车公众号
搜索:autoifeng

-

官方微博
@ 凤凰网汽车

-

手机应用
凤凰网汽车&凤凰好车


.png)







.pn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