任芙康:从“洋马儿”到“四驱”(上)|《车轮上的惊心动魄》
【导语:有一天,自己手扶方向盘,驾台大客车,急驶于山间公路,左转右拐,顾盼自得,却恍然发现,人躺床上,又是一个梦。】
撰文|任芙康、编辑|钱蕾
一
老家一带,自行车俗名“洋马儿”,官称脚踏车。七八岁时,我已有心思,对骑车人羡慕不已。终于等来机会,骗腿上座,一通猛蹬,耳畔风声呼呼;又似乎觉出,蹬踏的是身上一床被子,便明白,刚才做梦了。初学骑车时,腿长不够,将右脚别进去,半圈半圈地踩。会了单车,不知足,兴致转移,出门只瞧汽车。有一天,自己手扶方向盘,驾台大客车,急驶于山间公路,左转右拐,顾盼自得,却恍然发现,人躺床上,又是一个梦。梦后数年,如愿以偿,果真开上汽车。我因此相信,白昼有见、有闻、有思,夜来会有回报,往往还你梦景。

话说入伍进军营,新兵训练结束,团动员股股长宣读分配名单。抗美援朝归来的股长,不苟言笑的脸,棱角分明的嘴,一言九鼎,让数百名新兵,三下五除二,有了分门别类的去向。股长嗓音雄厚,却分明声声悦耳。令人向往的汽车连,成为我与二十九位新兵的归宿。听诊器、方向盘,半斤对八两,在漫长年月,就谋生而言,最为吃香。这意味着,这帮伙计未来饭碗好找,真乃人生刚刚起步,便是曙色晃眼。
到得汽车连所在东营房,下车刚解散,旋即又集合,由连长宣读“教导排”组成。一位排长,六台车,六名教练,每车五个学员,一一应声亮相、入列。接着是指导员简短的训令:敌人亡我之心不死,时刻进入战备状态;驾训从实战出发,三个月毕业;验收标准非常简单,各种道路、各种气候、各种时辰,一声令下,能开得动,能跑得快;凡考核未过关者,不予补救,另行分配。最后一句,将他开初的笑脸,减色一半,给人蒙上几许暗影。
当日下午,两辆嘎斯、四辆解放,将我们拉到团部大楼南广场。嘎斯系苏制卡车,车身小;解放为长春一汽生产,车身大—个子高矮的学员便都各得其所。六车各占一块地盘,班长(新兵对教练的统称)开始上课。先从车头保险杠、大小灯开始,让学员逐一辨认外貌。然后进入驾驶室,指认表盘、方向盘、离合器、油门、脚刹、手刹、变速杆......

连长、指导员亲自督阵,轮车观看,偶尔直接对学员指点。也就一个多小时过后,各车开始由班长做启动示范:如何松手刹,如何挂挡,如何踩油门,如何前行,如何制动......班长言传身教一番,换坐副驾位置,让学员逐一上车仿效。
我所在车的教练,是位正式班长,山西闻喜人,1965年当兵。但他不带晋地口音,一嘴北京南口调,说事直截了当。先就告诉五位弟子,咱这解放,出厂不久,而嘎斯老旧,淘汰货,没戏;开车这事儿,算个技术活儿,但门坎不高,熟练工而已,各位尽可放松云云。我直觉相信,碰上了好师傅。收工时,五徒皆欢,一个下午,居然人人都能将汽车开起来了。其他五车,亦都顺利,教学进度似有并驾齐驱之势。第二天上午,全排出发,六车相跟而行,全由学员驾驭。出乎意料,车队未去广场,而是开出营房,上了南(口)阳(坊)公路。此路不宽,车辆稀疏,几无行人,时遇骡马大车。表面看学员掌盘,但纯属木偶,一举一动听从班长发话。如前路清爽,会说踩住油门、匀速前进;如远见来车,会说松开油门、打轮、回轮;如需车速更慢,会说点击脚刹,乃至靠边停住。
如此这般,学员事后交流,方知各车情形大同小异。仅摸车一天,便上公路游逛,轮换下来,无不汗透内衣。六位班长,各有性情,有的耐烦,有的急躁。后者往往改锥在手,稍不如意,便会敲击学员挂挡的手背,多属象征性吓唬,有时亦带出恨铁不成钢的狠劲。回想当年这批战友,南人北人,均韧性不差,碰到不习惯讲道理的班长,皆能忍气吞声。
南阳公路盘桓数日之后,全排来到一处山地,是团里的坦克训练场(近日恰逢坦克停训)。排长告诉大家,作为装甲部队汽车连,到了真刀实枪那天,就得拉上物资,紧随坦克进退。放眼方圆三四公里,漫长的坡,陡峭的坎,不成路的路,不像河的河。坦克习武的地方,大块头尚需“硬着头皮”,今让汽车攀爬,新兵个个心虚。明摆着冒险,侧翻倾覆,应是“易如反掌”。但在班长们的指令下,或猛踏油门,急速冲顶,或缓击脚刹,从容下坡。连续三日,跋山涉水,竟如履平地,人未伤,车未损,圆满完成课目。这一下,艺高胆大的六位班长,成为新兵臣服的英雄,个个都相信,上得车去,一招一式,不折不扣听令而行,定会顺风顺水。

又一个早晨,教导排车队奔八达岭而去。此地乃万里长城千秋精华,京城北部顶级屏障。部队驻地至八达岭,为京张(北京到张家口)咽喉。公路穿过居庸关,与詹天佑建造的铁路相伴而行,正是遍布窄道、陡坡、急弯的二十几公里路程,扼守北京北部唯一通道。山西东北部、内蒙中南部、河北张家口,辽阔区域进京,悉数于此“签到”。车流量巨大且多为载重卡车,堵车成为常态,为当时北京地区一景。我们的固定线路,翻过八达岭城门,在延庆县地界调头。一路滞留,车慢如牛。有一天,凑巧三个事故,从山上回营房,竟费时四个小时。可班长另有说辞:你们就偷着乐吧,赶上了驾训黄金地段。有过数日经历,感觉确实如此。比方,下长坡时,切忌为省油而空挡滑行。上行遭遇塞车,且走且停,万勿发急,恰为学习起步的良机。左手掌方向,左脚松离合,右手松手刹,右脚踩油门,四肢并用,相互配合,如车无后溜,稳步前行,往往会听到班长连声叫好,能让人快活死也。我们还记住他一句告诫,山间行车,一旦有事,宁肯上山吃草,不可下河洗澡。
二
野外的平路跑过了,山路跑过了,该开车进城了。这城,就是北京城。
进城那天,连长、指导员双双到场,分别沉脸训示。兄弟们皆无日记嗜好,那天实在是值得记上几笔的日子。新兵绝大多数初次进城,居然“自驾”,兴奋中夹杂惶恐,自是在所难免。
从营房出来,行驶二三十公里,轮换一次。车到北太平庄,靠边停下,排长宣布,车队解散,诸车各自为战,跑完规定路线,单独返回。再登车时,方向盘轮到我手。往前一看,便觉太平庄忒不“太平”。一路南行,如履薄冰,躲人避车,直达西单路口,右拐,上了长安街。当年大车、小车身价平等,载重卡车除王府井一小截(灯市口至长安街)禁行,其余街巷皆可穿越。但见自行车东来西往,如过江之鲫,而机动车行驶线内,则路宽车稀。公交车亦不多,偶见三几辆,无不人满为患,隔着玻璃窗,能感觉乘客黑压压挤作一团。

临近天安门,有点开小差。眼光正往左前方的城楼攀爬,忽听班长一声断喝:“停车!”我右脚刚上刹车板,脚面便被重重压上一脚,这才见前面岗楼上端亮着红灯。一位交警跳下来,手指班长:“怎么叫新兵开车?”班长摇下车窗(居然不下车),陪笑解释:“我是想等繁华地段换他。”对方大为惊诧:“什么?繁华地段?全世界有几个天安门?”我早已跳下车来,这才细看,浩大广场与车道连成一片,无任何栅栏分隔,视野无碍,于我们新手而言,极容易对信号视若无睹。但交警的质问,开始超越红灯绿灯,班长不想罗嗦,便下车换我。班长上车,我以为他会皇逃窜,未料开出一段,似乎也就四五百米,刚到公安部大门附近,便一脚停下,令我再上。“这,可以吗?”我余悸未消,迟迟疑疑。班长瞪我一眼:“少废话。”他显然不在意交警(当时公安对白牌军车客气有加),怕只怕耽搁市区训练的金贵时间。
我重新驾车,朝东跑了一阵儿,长安街突地变窄,前有路牌:大北窑。班长指令左拐,途径呼家楼,我被轮换,车子继续北去。忽见路东一片高大建筑,名叫“全国农业展览馆”,坐落于庄稼地旁。远处,一二村落若隐若现。同一道上,三五马车悠悠赶路。如若巧遇夜里的清风明月,怕是会让人泛起思古幽情。顾不上多想,只是感叹这馆舍选址高明。参观“农业”的展览,进入真实青纱帐,闻到泥土气息,自然叫人可信、可靠。
不几天,教导排转入“以运代训”。每天辗转于市区、郊县,帮助地方单位拉运货物,学员兼任装卸。“东家”很划算,我们也愉快,因无一例外,每个单位都有好饭款待。
一跑才知道,北京周边,各县地盘都小。比方,出得昌平,朝东,刚把气喘匀,车已进怀。右拐南行,眨巴眨巴眼,路牌又换作顺义。这与我老家截然两样,相邻的甲县县城到乙县县城,全得仰仗长途客车,翻山越岭,短则半天,长则整日。
有前一阵子驾训垫底,我们这帮人,个个都觉得自己“会开车”了。其实,光是会开,只算进门。真本事在于,车子抛锚了,故障出在电路,还是油路?你又如何判断、排除。每天跑车,老有这里那里的故障,班长边讲边做,让我们每学懂一点,便增添一分虚心。
三
又过几日,接连跑了两次长途。先是去天津。京津公路属国道,但欠宽,来往货车又多,会车必得减速。跑了三个来小时,在一个叫河西务的镇上,吃了烩饼。继续赶路,天黑进得天津市内,满大街路灯亮起。这是座令人费眼的城市,绝无北京、成都的方正,有的岔道相交,出现五个以上的路口,让初来乍到的生客,彻底无所遵循。又发现此地人良善,我们一路打探,男女老少,皆殷勤指引。相遇几辆有轨电车,稀奇如旧上海的电影镜头。峰回路转,终于到得火车东站后身一家工厂。依照在北京各单位的惯例,都是先卸车后吃饭,否则肚饱无劲儿。但主人死活劝住我们:“吃了再说。”头一回,油焖大虾、海螃蟹管够。饭后出来一看,几车货物早被一帮男工女工,卸个一干二净。

第二趟长途,去河北交河县一个叫富镇的地方。在门头沟一家煤矿装上六车焦炭,一路南行,到了河间县地面。那一带的公路路基宽宽大大,但让人纳闷,柏油只铺两车宽的路面,其余部分为夯实的黄土。所谓“夯实”,实际上并不合格,头天刚下过一场暴雨,黄土部分已经泡透。
我们这车殿后。车厢上“赋闲”四人,焦炭上铺上草垫,围坐聊天。四野辽阔,让闲谈无边无沿。突然,对面似有来车,我车偏右避让。没料到的是,偏右,继续偏右。实际上,前后右轮均已脱离柏油路面,顺土基前滑,再无回轮希望。学员肯定已踩了刹车,但刹车导致加速偏右,直至翻出路基。一沟深水,托着车子缓缓侧翻。焦炭密度小,气孔多,整车倾倒入水,便好似沸水蒸腾。水气弥漫中,一时不辨西东,场面甚是惊恐。幸亏车上我等四人,个个都会凫水,无不手脚麻利,奋力游了出来。
车内二人,则完全淹没水中。我们先拖出开车的学员,再拖出班长。班长居右位,喝水最多,连咳带喘,脸色发青。学员站在公路上,一言不发,双腿不停颤抖。
就像上天安排,附近恰好有个规模不小的农机站。出事不过十来分钟,四十多岁的站长(汽车兵出身)带人前来搭救。他与班长正商量拖车,排长也开车寻来。很快,排长、班长都表示,全听站长指挥。站长布置手下开来两台“东方红”拖拉机,并排停妥,拴牢粗粗的钢缆绳。在他的手势指挥下,双机同时启动,徐徐发力,我们的解放露出水面,靠近渠岸,缓缓上坡,最后稳稳定在公路正中。整个过程,不动声色,一气呵成。本来鸦雀无声的现场,突然间,爆发出一片欢呼。我这才留心四顾,吓了一跳:围观的大人小孩,怕在千人之上。
过了半个多小时,水已控干,站长示意班长上去试试。只见班长一扭钥匙,着了;然后挂挡给油,动了。出了如此大事,人车无恙,众人啧啧称奇。只丢了一车焦炭,站长说他回头组织打捞,并断然拒收排长赠送站里五十元的酬谢。
临行前,排长带我们列队,向站长和他手下敬礼告别。赶到富镇,已近深夜。镇领导一直苦等,用几桌大鱼大肉为我们洗尘、压惊。席间来言去语,全是上等好话,什么逢凶化吉、化险为夷、吉人自有天相之类。也有算命般的道喜,大难无事必有后福云云。我向来不信这些祝福,然而那晚,但觉句句入耳、顺耳,以至虽无酒量,却逢人举杯。
第二天,休整一日。恰逢富镇赶集,西瓜摊位步步为营。闲逛中,说到这场事故,头天毫无恐惧,过了十多小时,反倒生出后怕。如果翻车刹那,凑巧了呢,几吨焦炭将我们埋入水底,岂不呜呼哀哉?
但实际上,翻车对我们心理影响有限,并未蒙上死而复生的阴影。说来还是年轻,转天便没心没肺起来。本来就是坦克训练场习得的手艺,返京途中,只要路况稍好,依旧动不动跑出六七十码的速度,让卡车撒野的异响,像毛头小伙一路招摇:“我来了。”
(未完待续)

作者简介:
任芙康
四川达州人。曾任《文学自由谈》《艺术家》主编,天津市写作学会会长。现任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。著名散文家、评论家。作品散见各大报刊。享受国务院专家冿贴。曾任郁达夫小说奖、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评委,第七届、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。
驾龄:50年
曾驾车型:军用卡车、普桑,现驾车为帕萨特
(本文系《禾颜阅车》原创,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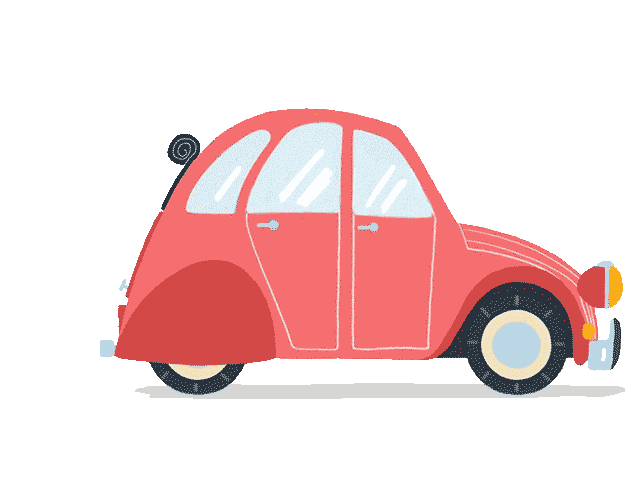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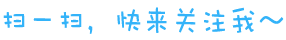

-

凤凰网汽车公众号
搜索:autoifeng

-

官方微博
@ 凤凰网汽车

-

报价小程序
搜索:风车价


.png)







.pn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