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斐儿:我的移动“孤岛”(上)|《车轮上的惊心动魄》
【导语:一场告别或者自我救赎,很多时候是在车里完成的。汽车密闭的狭小空间,为人构造了一个密闭的幻觉空间、一种保护,让人回归自我本身,暂且忘了车门打开的一刹那依然将一脚踏入兜头而来的尘世喧嚣......】
撰文|吴斐儿、编辑|钱 蕾
序
一直以为“逃离”的同时,也是“抵达”。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没有尽头的迁徙的过程,从一个泊岸赶往另一个泊岸,从一个孤岛奔赴另一个孤岛。当另一头的泊岸无从显现的时候,我们习惯称那个遥远的方向为“彼岸”。人人都是“行者”,生生世世,亘古如斯。

没有人会忍受长时间停留在一种时空,三维时空中的“时间”永远在流逝,下意识地改变“空间”,成了人类集体记忆中对抗平庸的方式。工业文明锻造的成果—蒸汽机以火车和汽车的发动机的诞生作为标志,像草籽一样撒播在人类世界,于是,一台台汽车发动机引擎如机械心脏,与人类的心跳相互咬合,成就了人类主宰空间的移动路线、移动速度、移动关系最自由、最个性化的手段。
没有人会拒绝速度,就如同没有人会拒绝自由。人与车,都成了随时迁移的移动孤岛,在岁月的荒漠中寻找绿洲和泊岸。
扶桑在东
一场告别或者自我救赎,很多时候是在车里完成的。汽车密闭的狭小空间,为人构造了一个密闭的幻觉空间、一种保护,让人回归自我本身,暂且忘了车门打开的一刹那依然将一脚踏入兜头而来的尘世喧嚣......
和第一任男友分手之后,我给自己完成的“我很好,我可以的,重新开始吧”这样的仪式就是与我的第一台车共同完成的。当然这个仪式在完成之前,有着漫长的准备期,正像天下很多无疾而终的情感一样,你将在很长一段患得患失的情感里煎熬,过着脚踩云朵一脚高一脚低的日子,没有人会告诉你你和他的关系会何去何从,没有人会代你体会命悬一线的感觉。夜里深沉的失落会被日出时的光芒驱散,自我安慰取得的暂时性安宁,也会被一首老歌的旋律摧毁。
他去日本之前,我就预感到我们的关系会变得不一样。女人头上有着三百万根触须,能够毫不费力地捕捉到除却语言之外的东西,包括温和眼神隐藏的去意,这个很难被解释,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暗物质吧。
他签证是三年期的,可以多次往返,说是等那里的生意安定,就会经常回上海看我,他说的时候很坚定,我听的时候很安静。也许成熟的分手就是这样,从“疾速”到“停止”有一个缓冲地带,在这个地带中,两人都会变得安静下来,共同为分手画上一个体面的休止符。我们照常去常去的咖啡店喝咖啡,小店的外面可以停车,这成了我们常去最大的原因。小店的墙上挂着很多老上海的照片,外白渡桥、外滩、城隍庙、醉白池......很多地方我们都没
有来得及一起去。靠墙的窗子用洗烫得很干净的红白格子布垂着,傍晚的夕阳有后劲地透射过来,映照在他的身上,勾勒出他令人心生心动的轮廓,脸部的线条漂亮得令人不安,那是一种具有攻击性的美,浓密的眉毛下面有着一双湖面般闪烁的眼睛。这样的一种美,也要告别了吧,我对自己说,多看看吧。
我盯着他,眼睛在湖面荡漾,他的眼神不去接。你看,人与人交流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语言,语言是那么多余那么空洞,只有当时当刻微妙的感应,才烫手得真实。

“有空可以去学个驾照,今后自己开车也不赖。”他把续的咖啡旁边的糖块拿开,那么多年他依然那么自律,不去吃这些糖类和油炸食品,身材保持得很好。我对于他穿白色衬衣有着一种深深的迷恋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副躯体,充满着对抗俗人俗世的克制的力量。我瞬时觉得我已成为他的糖类和油炸食品了,心里想着如果都分手了,还用管我这些么。
“我教你认识一种花好么?”他拍拍我的肩,这个动作我很熟悉。我想到我们第一次和同事到卡拉OK去唱歌的时候,我唱的就是这首歌,“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,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,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他到来,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......”旁人打趣,谁准备拍你的肩啊,然后他就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,我转过头望着他动弹不得,旁人哄笑一团......这一刻仿佛就像在这爿小店墙上的画一样定格了。
那天晚上他开车送我和同事回去,车厢顶的车窗被打开,夜色成了头顶的露天电影院,梧桐叶子在夜色里触手可及,一排排楼房飞速掠过,万家灯火的城市显现魔幻般的野蛮生长的力量,我一直昂着头看,车里循环播放着田震的《野花》,“摇摇摆摆的花呀,它也需要抚慰,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......”影像飞逝和歌声形成了一种即兴的表达,那一刻,我放下了自己的清高和做作,也是在那一刻,我觉得人该拥有一部自己的车,最好是开着窗顶的那种,当然还有一个可以拍拍自己的肩就听他安排的人。
小店的墙外有靠墙的扁扁的花坛,我被他牵着走出户外,他蹲下来,看着我,眼睛含着光令人伤神,“你认识这种花么?”我摇摇头。“她叫扶桑,东渡扶桑的扶桑。”他看着我,递给我一套日本西阵织的和纸,那是手工打浆纸张的极品,纸纹细腻得让人恭敬,他让我想他的时候给他写信。方才屋里喝咖啡时的空气凝固起来,那一刻,显得那么不真实,我听见心中的湖面冰裂的声音传来,清脆而孤绝,余音不存。
他终于还是走了,像是一种解脱,对于他也对于我。不确定是危险的,到了某一个时刻,它一定会出现一种倾向,一种泾渭分明的清晰局面。他会有电话来,声音还是那个声音,人已不是那个人,我也会期待他的来电,但开始不再做下次来电的预期。我躲藏在风平浪静的生活的后面,日子出现了某种断层,过去的生活脱轨而去,新的轨道尚未铺设,有一种阳光下的暗无天日的感觉。我也知道这样的刑期有朝一日会结束,但不知道哪一天会来,我对自己强压下的平静的痛楚非常痛恨,又无计可施。
一天晚上加班晚了,为了躲雨,我干脆就留在单位发呆,办公室空空荡荡,嘈杂的声音隐匿遁形,我干脆打开电脑放歌,田震的《野花》四处弥漫,附着在地板上、天花板上,缠缠绕绕、枝枝蔓蔓。我冲了一杯咖啡站在落地玻璃旁,看着雨滴肆虐地敲击在玻璃上,形成了巨大的泪痕,我对自己说,是时候该改变了。我关上电脑,把手机和钥匙包在塑料袋里扎紧,捆绑在腰上,
脱掉外套和皮鞋,只穿着一件T恤和牛裤,来到写字楼大堂,在躲雨的人和大楼保安的错愕注视下,一猛子扎进了雨里。我声嘶力竭用尽全身力气放声大唱“摇摇摆摆的花呀,它也需要抚慰,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”,商场门檐下躲雨的男孩抱紧了他的母亲,公交车里半个车厢的人瞪大眼睛。我来到车行的玻璃橱窗门口扒拉着玻璃,看着一辆辆锃亮的汽车像崭新的野花一样等待着被我采摘,心生爱怜,直到保安把我轰走。我继续高声歌唱,任由身边驶过溅起的雨水把我浇透,胡乱地抹着雨水,痛快的淋漓的雨水,还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本来样子,此时与我的破嗓音融为一体,我和世界在长达近一个钟头的“雨中漫步”中和解了。

回到家后,我大病一场。大病初愈,万物回春。我起身梳妆打扮,喝了给自己煮的红茶,穿上了一套红色的连衣裙,踩着高跟鞋来到车行,订下了人生第一辆带车顶窗户的车,我清楚地记得它的型号—尼桑蓝鸟,是黑色的,我坐进驾驶室,像一朵红色大丽花在黑色箱体中盛放。然后我按部就班学驾照、找二手车练车三个月,当我到车行提车的时候,对着那晚赶我走的保安莞尔一笑,那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句号。那一天,我更换了手机号。
时间滑走了一年半,清风有序,日月安宁。一个周末我驱车到了金山海边,海水像一块巨大的果冻上下起伏,像心跳,我没费多少劲就爬上了车顶,拿出了一个收纳盒,里面有我和他认识这几年交换的信物,当年令人屏息的物件,今天没有了丝毫生气,失去了精神的宿主,它们也没有了魂魄。我站在车顶极目远眺,海风一下子把我罩住,像是进入某种风口的隧道。我把当年定制的刻有两人英文名的手链拿出来,用尽全力抛向大海深处的方向,脱手的那一刻,那条细细的手链瞬即无影无踪,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,那种感觉很是奇特,让人感受到人与人相恋一场的虚无。
我拿出了当年那沓他送我的和纸,没想到第一页和纸的底部有两行字,不细看还看不清楚,风吹得和纸凌乱风舞,那是他的笔迹—分手的时候,带她(他)去认识一种花,因为花每年都会开。字旁边还印有一丛花,细看发现是扶桑花。
(扶桑花叶似桑而略小,有大红、浅红、黄三种,大者开泛似芍药,朝开暮落,落已复开。扶桑木两两同根偶生,更相依倚。)

【作者简介】
吴斐儿
剧作家、诗人、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、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、新华社《瞭望东方》城鉴栏目撰稿人;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、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扶持优秀编剧;创作的诗歌、散文,在《上海文学》、《四川文学》、《红蔓》、《上海作家》、《上海诗人》、《诗刊社》《中华朗诵》等刊物发表,并有舞台剧《破晓之光》、沉浸式话剧《那年桃花》《渔阳薪火》《营救》《宋庆龄和她的孩子们》《军号手》《童声嘹亮》等。
驾龄:20年
曾驾车型:宝马X5、丰田凯美瑞、路虎
(本文系《禾颜阅车》原创,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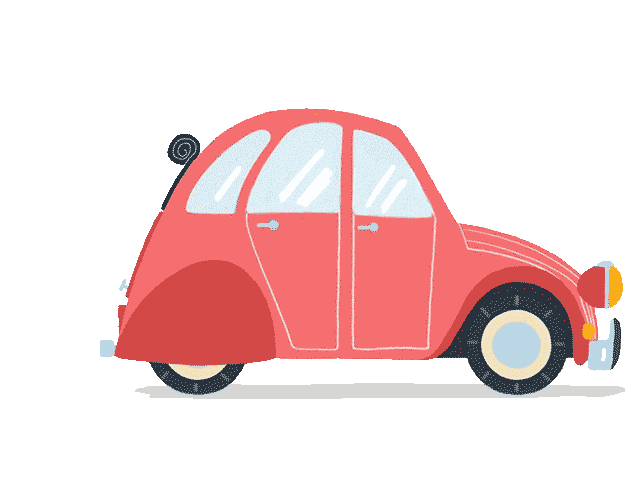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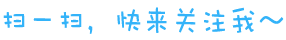

-

凤凰网汽车公众号
搜索:autoifeng

-

官方微博
@ 凤凰网汽车

-

报价小程序
搜索:风车价


.png)







.png)